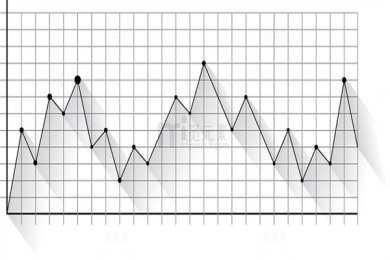多伦多大学艺术史系博士候选人钱文逸
JacquelineJung,EloquentBodies:Movement,ExpressionandtheHumanFigureinGothicSculpture,YaleUniversityPress,July2025,340pp
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的中世纪艺术学者雅克琳∙容格(JacquelineJung)于2025年7月出版的《雄辩的身体:哥特雕塑中的动态、表现与人体》(EloquentBodies:Movement,ExpressionandtheHumanFigureinGothicSculpture,以下简称“《雄辩》”)是笔者自疫情以来在欧洲艺术史领域最翘首以盼的新著之一。无奈该书出版之际,本校图书馆的新书购买程序已按下暂停键,笔者不得不苦苦等待跨校借书系统重新开启近一年,终于在第二年暑假从蒙特利尔大学处获得了一个月宝贵的借阅时间。读罢确认,这着实是一本值得推介给国内学界、反映海外学科前沿动态的精心之作。
从“图像程序”(pictorialprogram)到“感知进程”(perceptualprocess)
随之而来的,是对图像或雕塑程序(pictorial/sculpturalprogram)一种全新的定义。以往——尤其以图像学(iconology)为框架的认知——将图像程序视为一个静态的多单元结构,而美术史阐释的目标即是去揭示这一结构内部各单元之间的关系,以此完成对整体意涵的统领性解释。一种基于在时空中延展的实地体验的图像程序则不将整个结构视为静止不变的整体,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占据了具体物理空间的环境,把观者在这一环境中由一点至另一点的运动视为一种体验性的线索,运动中对同一程序在不同角度的观看与感知构成一个连绵不断的印象序列,这一变换中的观看与感知把原本被定格的程序(program)转化为一种动态的、在不同面向中展开的感知进程(process)。图像程序由此收获了动态和多面性,这不仅为雕塑群的形式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更丰厚的原始素材,也带来了更开放且具包容性的含义阐释姿态——意义的“灵活性”(flexibility)是容格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这种灵活性正得益于观看本身的动态。
从某种角度而言,动态观看和雕塑的空间性并非美术史的新议题,甚至在一些领域已是老生常谈。但容格的过人之处在于,用细腻而专注的感知力为这一人尽皆知的学科常识增添了一道新颖而系统的纵深。这种系统与深入却不流于教条或刻板,而是依据具体的分析案例和其空间特性尽可能结合不同的观看动态——从环绕雕塑的有效视点中抽取出的多个观看角度,雕塑在不同距离和仰视角度下呈现出的不同形态,不同雕塑在同一空间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等等。同时,容格的分析尤为强调作品与观者身体共同占据的物理空间和两方互相作用的观看经验,这反映出其对现象学理论的深切投入。她在书中强调了“图像”与“现场感”(image/presence)这一成对概念,倘若静态的程序将雕塑定格成图像,那么动态感知中的雕塑则是作为一具躯体与观者的躯体相遇,它的第一属性是一种物理的、经验的在场。在任何对其意涵的剖析之前,研究者都必须全面而开放地捕捉这一鲜活的“在场感”。这便是贯穿《雄辩》的方法关怀。
虽然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观看实践并不一定与容格提出的框架对应,也并非所有类型的作品都如此强调多视点的互动性观看,但在明确具体研究对象的文化情境的基础上,本书的倡议可以构成一种丰富作品视觉内证的基本策略和思想实验,对各类需在实地考察的美术史素材都具有相当的启迪意义。中国美术史内部的此类素材就不在少数,从具体环境中的佛教造像到各种具有公共仪式功能的图像程序,不一而足。
在这一轻微的短缩视角下,主要人物组的头像之间的间隔缩小了,人物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紧密;圣母的身体更自然地休憩在床上,而彼得的手臂与其说是把圣母的手臂撑立起来,不如说是提供了一定弧度的承托。此外,床深邃的底切边沿在这一视角下显得更突出,强化了人物占据一个具有纵深的空间的错觉。(66页,图一、二)
图二:圣母沉眠浮雕(地面仰角一)
倘若这份1927年的分析仍然停留在静态的实地观看上,容格则很快就把视点投入运动中去。她先是跟随信众进入教堂的常规行进路线,继续向入口走去,在这个距离更近的仰角下,浮雕的整体视觉呈现仍然成立,叙事中男性参与者的脸成为主导,人物的身体姿态亦显得更为迫切。容格尤其注意到,圣约翰的面庞在其他视角下均被他哀悼的手势遮蔽,只有当观者行进到这一位置才真正浮现出来。这一动态观看经验中的转折为圣约翰本人所体现的情绪加入了一个浮动的因素,它将手势与情绪的关系从一种一对一的固定状态中解放出来,促使观者调整对其哀悼情状的体认。(图三)
容格甚至不满足于从正面仰角观看这件浮雕,而是参照中世纪列队行进的路线从左右两侧继续展开分析。从右侧看,圣母主要被三位承托她的人物形象所环绕,她的身体重心向下,“被锁定在人性悲悼情绪的社会界域中”;从左侧看,圣母与龛楣上方敞开的空间之间则开启了一条通往天界的通道。两侧所呈现的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关系标记出“圣母从哀伤通往荣耀的道路”。一件浮雕所表现的情感与意涵的灵活性便在这些相异却共同存在的可能性中生长着。(69页,图四、五)
图三:圣母沉眠浮雕(地面仰角二)
图四:圣母沉眠浮雕(右侧仰角)
图五:圣母沉眠浮雕(左侧仰角)
图六:马格德堡大教堂入口处,聪明与愚拙童女雕塑面部表情的重组排序,153页
需要指出的是,再媒介化不仅体现在对作品的视觉呈现与分析上,还深切改变了阐释学本身的实践。最能体现其成功之处的是第二和第四章中的两段精彩解析,有趣的是,这两个案例均包涵一组具有一定对立性的雕塑——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入口处的是一对象征基督教会(Ecclesia)和犹太会堂(Synagoga)的女性化身形象,在马格德堡大教堂(MagdeburgCathedral)是一组表现聪明童女与愚拙童女的雕像(WiseandFoolishVirgins)。在这两组材料中,容格的阐释策略包涵几个步骤:她先是打破由照片和道德喻义阐释所建构的人物之间的“静态对立”关系;再通过动态观看挖掘具体人物形象复杂多变的物质形态与宗教意涵;最后,借由动态延展开的多元意涵对雕塑组中长期与负面涵义联系起来的人物形象(也即犹太会堂的人格化身和五位愚拙童女的形象)进行一种更富人性化的解读。这种解读最终落脚在中世纪观者与这些负面形象的情感联结上,也即,面对这些被排除在基督教正统教义或宗教救赎以外的形象,观者是否有可能产生拒斥、否定等负面情绪以外的更具建设性的感受?倘若这些人物也同样是人性代表中的一员,渴望救赎的信众能否与她们产生片刻的共情、认同(“心变柔软的过程”[softeningoftheheart],89页),并从中对教义形成更丰厚的理解?容格深知中世纪宗教艺术中长期存在用视觉文化制造不同信仰群体间分裂与敌意的案例,但她通过对动态观看的关照找到了一种更开放更富人文关怀的立场,也为宗教艺术中所体现的具体历史情境内的情感观念提供了新的视觉素材。
图八: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南部耳堂入口处,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人格化身雕像,正面平视对照图(发表于1901年)
更进一步来看,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入口处的这对人格化身雕像长期在照片中并排对照呈现,但在实地的空间经验中,她们实际分列在教堂入口的两侧,相互之间不仅间隔了两个门道,还有包括龛楣浮雕和门间柱雕像等环境装饰(图八)。把这两座雕塑重新放到这样一个开放空间中,并考虑信众游行的路线和角度,静态对比的确凿感旋即瓦解,这两座雕塑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复杂而生动。在对犹太会堂这一形象的分析中,容格用观看的动态消解传统图像志阐释对人物属相(attribute)的定性。她以雕像的五边底座为选取观看视点的参照,拍下数张连贯的照片(图九)。将它们串联起来阅读后会发现,分列在雕像两侧的折断的长矛和写有摩西律法的石板不再是静态的符号,而是随着观看视点浮现又隐退的结构性元素,而这一此消彼长的进程中,属相与人物本身的关系不断浮动。诚如容格在这段分析的结尾所说,“眼盲与肉欲,断裂的长矛与律法的石板——我们在这一组紧凑的属相中看见的并非一边倒的贬低,抑或对负面符号过度决定的堆砌,而是因因果果星丛般的汇聚”(78页)。
或许是因为对瑙姆堡教堂中这组雕塑的研究汗牛充栋,给学者留出的阐释空间已经不多。容格此处更多是对现有的不同解读做出一种兼容并包的整合与重组。但这也展现了当前美术史研究中对思想开放性的诉求,研究和阐释的目的不再是得出一个决定性的单一结论,或提出一个标新立异的指导性视角,而是打开一系列供思辨周旋与探索的空间。
把瓦尔堡作为方法:史学史余绪
图十二:阿比∙瓦尔堡
图十三:《记忆女神图集》,1927年汉堡瓦尔堡图书馆内讲演配套展示
这种学科范式的转向在容格的新作中同时体现出其积极与需警惕的面向。本书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对四个核心案例的分析并未采取统一模式,而是参照每个案例的空间属性“因地制宜”。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入口的雕塑环境是一个以完整建筑立面为背景、结合了不同雕塑媒介(浮雕、全身雕像)的整体程序(第二章),容格在这一章的分析里侧重观者不同路线和角度的行径如何影响对其中不同元素的体验;从这一入口进入后出现的一根雕有多个天使形象的长柱则是一个可以从三百六十度环绕观看的单个结构元素(第三章),这一章的策略也就转为从可供信众站立的不同视点来观察长柱上的雕像;马格德堡教堂入口处的十个童女则是一组整齐集中排列在空间定点上的完整人物立像组,容格在此处把议题从动态观看转向人物的情感与情态,恰恰因为情感在这一题材的叙事表现中占据核心位置(第四章);瑙姆堡教堂中的敬献者分布在一个开阔的宗教室内空间的各个角落,面对此种雕像与空间的关系,容格不得不采取“解构”立场,把各种视觉讯息打散后进行二度整合(第五章)。
此外,本书第三章中对立柱上多个雕像的分析或许也展现了动态观看和空间视角作为研究范式的难点与局限。一方面,容格深谙具体空间中礼拜仪式的特性,也因此挑选出几个“仪式热点方位”(liturgicalhotspot)作为着重观察和分析的依据。但阅读论述却难免感到,面对这个需要环绕一周观看的多人物雕像立柱,观看视点是无限的,如何挑选、在具体视点究竟“看什么”其实极难把握,而语境证据恰恰可以提供一些更明确的限定。或许,容格所提出的方法范式在将来的研究中所需的也是更多样的尝试,引入更多语境信息是否可以帮助研究者进一步缩小和合理限制动态观看本身的多变与不定?分析中经验层面的描述与历史语境的结合和调配还可以如何调试?
图十四:巴克森德尔,《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椴木雕刻家》(1980年)封面
再者,就本书提出的方法而言,容格全然略过巴克森德尔(MichaelBaxandall)在《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椴木雕刻家》(TheLimewoodSculptorsofRenaissanceGermany,(图十四)一书中开拓性的分析,多少令人有些遗憾,毕竟巴克森德尔是较早强调多视点观看及雕塑作品情绪与涵义之多元性和灵活性的学者。这种忽视在瓦尔堡复兴的背景下是可以被理解的。作为瓦尔堡学院后期强调社会语境和语文学分析的学术大家,巴克森德尔在动态观看方面的阐释极为克制而审慎,他缺乏瓦尔堡图集中那种冲破时空地域边界的想象力和穿透力,也不会在研究中主动依托“动态影像”“蒙太奇”等概念。从某种意义而言,容格正是借助瓦尔堡复兴所带来的学科转向,将巴克森德尔引而不发的零星洞见转化为一场淋漓尽致的感知盛宴。而这一研究方向的潜力长期得不到全面释放,究其根本是巴克森德尔工作时整体的学科环境与趋向所致。
最后,笔者想以本书为契机谈一个与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息息相关的议题作结。瓦尔堡对容格一书的重要性体现了欧美学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史学史反思要最终反哺到学科实践中,形成一种全面而成熟的方法重估和实践创新,往往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纵观欧美学界近五十年的发展,史学史研究与学科实践的问题意识之间的关系发生过几次重要的转折。倘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史学史研究本质上呼应了同时期对图像学等既定方法的不满以及新批判视角的引入,那么新世纪则出现了另外两个重要趋势。一是史学史作为一门次生学科乃至产业的兴起,在近几年,这一趋势更是从以往欧洲中心的框架蔓延至其他非西方艺术领域,呼应了学科内的全球转向;二是史学史研究内部分裂出两种有一定差异的取向。理论先行的一支更多是将对当前学科实践的理论愿景投射到对前人的理解中去,把史学史当作当前学科理论的资源,用之为当下学科转向做注。从某种意义而言,第一批史学史研究和瓦尔堡复兴的初期都存在此种去历史化的倾向。另一支则更加强调批判性的语境回溯,不再只将学科理念放在一个真空的思想脉络下去辨析,而是联系同时期政治生态、文化情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挖掘学科方法背后的种种观念性或意识形态动机。
在对欧美学界的观察中,我们须要认识到两点。其一是史学史作为次生学科产业的出现本质上也存在与学科实践断裂的问题,其实际作用是为领域内的研究者提供额外的发表和职业机会,在视野上往往局限在欧洲艺术传统内部,并没有很好地与非西方领域形成对话关系(这种闭塞状态因学科的全球转向有望取得缓解与突破)。其二是,多数史学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欧美学科内部的主流研究实践服务。对理论先行式研究的阅读必须体认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同时辨析此种问题意识在本土研究中是否具有适应性。相比之下,批判性语境回溯对全面了解这些学术前辈或许是更可靠的参照,其主要意图在更恰当地评估和审视以往学科内部出现的经典方法,以便后人(包括远在另一个文化情境中的其他研究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清楚地了解他们手中工具内含的种种风险和观念重负,帮助学科实践企及更高层次的批判性自我意识。容格一书在瓦尔堡复兴的浪潮中独树一帜,既是因为她跳出了史学史研究本身的藩篱,更是因为她真正对如何将瓦尔堡的诸多理念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方法洞见展开了大胆的试验,可以说是同类尝试中最为成功而彻底的一例。
鉴于国内美术史学科架构的复杂历史脉络,西方美术史学史与本土学科实践之间要想建立更有机的互动关系相对困难。不妨指出几个思路供各位师友参考,当然,这些提议必须建立在对本土学科核心素材及其文化情境深入思索的基础上。其一是尽可能少把重要西方美术史家仅仅当作一种研究和论述对象来看,因为对象化意味着取消他们指导实践的能动性,而应当多在阅读中抱持一种“学习心态”,让他们与我们、学科历史与当前研究在实践层面上保持一条敞开的转化通道。即便是老旧晦涩如李格尔,其对具体作品视觉结构的观察、分析与描写仍能启迪我们的观看与描述,仍包涵了这门学科自身思考与认知方式的一种基本生命力。其二是现有的史学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手中工具在欧洲学科建设语境中的原初意图和理念局限,并在运用中尽可能避免误用误解和重复前人错误,同时最大化转化的创造性潜力。我们既要继续深耕学科经典方法持续的生命力,又要清晰认识到任何一种方法和理论视野潜在的风险。此外,我们的“学习”应当以找出本土学科发展中所呈现出的种种不足为出发点,而应避免在缺乏考量的状态下承袭海外研究的问题意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让史学史研究能真正面向本土的学科实践,让那些经典美术史家不要沦为悬空的学科论述对象。
《雄辩》在充分开掘可为学科实践所用的新感知媒介的同时,亦反映出其中可能存在难以掌控的趋向。熟悉史学史的读者一定知道,这种在潜能与混沌间摆荡的辩证性正是瓦尔堡本人治学的核心特质,而在该作出版之后,亟待中外学界思考的或许是如何更好地让这种新的动态时空分析在限定中发挥其潜能。本书的最后一项启迪也在此:我们向学科前辈的学习——一种真正面向并最终反哺入学科实践的史学史反思——必然是一项无尽的志业。
(本文写作过程中与纽约大学美术研究所博士生陈允灏多次交换意见,特此致谢。)
校对:徐亦嘉